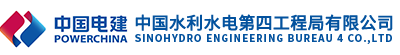梅雨季的脚手架 |
|
|
|
|
立夏后的雨总是下得犹豫。起初是疏疏落落的试探,像是天公在云絮间漏了针脚,直到檐角滴下的水珠串成了线,才肯彻底泼洒开来。我常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看雨,看那些灰蒙蒙的脚手架在雨雾里生长,钢管的接缝处沁出铁锈色的泪痕,倒比晴日里更多几分生气。 窗外的开关站正在浇筑第一层底板。绿网被雨水泡得发胀,像浸透的茶叶在风中舒展开来,滤下的雨丝都染上了苔藓的腥气。戴红色安全帽的工人踩着钢管搭成的骨骼攀缘,雨靴溅起泥浆时,总让我想起老家插秧时节的水田——父亲佝偻的脊背在雨幕中起伏,秧苗列队站成青色的诗行,而此刻脚手架上晃动的身影,正将钢筋编成另一种形式的五线谱。 打桩机的轰鸣裹着雷声传来,震得玻璃微微发颤。某个瞬间,深埋在混凝土里钢筋伸展的声响,竟与窗外香樟树抽芽的动静暗暗合了拍。这让我想起去岁深秋在工地捡到的半截钢筋,断面处密布的年轮状锈迹,与后山老松被雷劈开的伤口何其相似。钢筋工老周说,雨季浇出来的混凝土最结实,“水气渗进去,就和钢筋长出根来了”。他粗糙的手掌拂过模板时,总让我错觉看见农人抚摸抽穗的稻子,那些在模板中渐渐凝固的混凝土,何尝不是另一种形态的作物? 雨水把基坑变成了镜匣。新支起的模板倒映着流云,钢筋笼子泡在水里,恍若沉入深潭的青铜编钟。几个南方来的工人蹲在避雨处剥青蚕豆,碧玉般的豆粒滚进搪瓷缸,让我想起儿时在檐下和祖母捡麦稗的光景。那时候总觉得雨是能吃的,张开嘴接住瓦当滴落的雨珠,舌尖能尝出青瓦的涩与陈年稻草的香。此刻顺着安全网滑落的雨帘里,是否也溶着千里外故乡的炊烟? 最难忘的是那个暴雨突袭的深夜。探照灯切开雨幕的刹那,我望见安全网兜住的雨珠簌簌坠落,宛如某个巨型生命体在蜕皮。塔吊的红灯在雨雾中明明灭灭,像极了老家河湾的渔火。忽然记起《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说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那些在雨水中悄然拔高的楼宇,那些攀附着钢管向上蜿蜒的野葛,原来都在遵循着同一种生长的韵律。混凝土泵车的长臂伸向夜空时,我竟分不清浇进模板的是商砼还是液态的星光。 晨起巡视工地,积水未退的基坑漂着几片榕树新落的叶。穿胶鞋踩过颤巍巍的竹跳板,指尖触到昨夜新浇的垫层,水汽正顺着螺纹钢的沟槽往深处钻。恍惚听见父亲说过的话:“秧苗喝饱梅雨,秋天才压得弯扁担。” 放晴时分,塔吊长臂正把朝阳吊往云端。安全网上凝结的雨珠渐次蒸发,在钢管的丛林里升起虹色的雾。老周蹲在卸料平台边缘啃馒头,忽然指着东南角惊呼——不知何时,脚手架缝隙里竟冒出一簇灰灰菜,细小的白花在风里摇晃,像极了老家田埂上的那些。 雨水漫过基坑边缘的青苔时,我忽然懂得,所谓生长从来不分经纬。钢筋在混凝土里扎根,野草在钢梁上开花,打桩机的震颤与惊蛰的春雷原是同频的震颤。这个梅雨季,我们都在浇筑某种会呼吸的永恒。 |
|
|
|
| 【打印】 【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