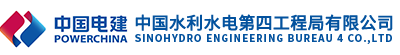风车上的月亮 |
|
|
|
|
山脊上的月亮是被风机叶片搅碎的。巨大的白色扇叶每转一圈,月光就被切割一次,碎银般洒落在我的脸上。工人师傅说,这儿的月亮比老家的跑得快——刚爬上东山头,一转眼就被风车赶到西边去了。 我眼中的月亮总是蒙着一层灰。它从吊车的钢铁骨架间挤出来,被纵横的钢筋切割成几何形状,最后才勉强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圆。同事说,这月亮比家乡的小了一圈,像是被谁咬掉了一口。 风电场的夜晚从没有真正安静。叶片划破空气的呼啸,塔筒在风中的嗡鸣,还有时不时响起的对讲机杂音,构成了这片荒岭独有的夜曲。工人师傅裹着沾满机油味的棉大衣,围坐在取暖器旁,中间摆着山下工友送来的夜宵。包装盒上印着“团圆”两个烫金字,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反着刺眼的光。 “已经五年没回家了。”坐在一旁的工人师傅打开夜宵包装盒说到,里面的油脂已经凝固成白色的霜。他手机屏保是女儿满月时的照片,现在那孩子应该已经会追着村里的孩子要糖吃了。上次视频,她对着镜头喊“叔叔”,怎么也不肯叫爸爸。 一百三十多米高的风机在夜色中缓缓转动。我突然想起老家晒谷场上的风车,此刻应该堆在仓房角落,挂满蛛网。母亲总说要把它搬出来,让月娘娘吹走霉运。今年她风湿犯了,想必又忘了这个仪式。 凌晨时分,我在值班室里透过玻璃窗看见月亮。它卡在两片扇叶之间,像被钉住的银币。手机亮了屏保是我的全家福,照片映出当时的笑脸。时常在想父亲身体是否健康,母亲的膝盖是否还在阴雨天作痛,他们总在电话里笑着说“都好”,却不知那刻意提高的声调,早已出卖了强撑的轻松。就像老家院子里那棵枣树,越是结满果子,枝干越要弯得更低些。山风穿过塔筒的检修门,发出呜咽般的声响。 山下的村庄偶尔闪过几点灯火。工人师傅说那是留守的老人在给月亮上香。我们这儿的探照灯太亮,把月光都冲淡了。在回去的路上,风机投下的巨大阴影缓缓移动,像表盘上的指针,丈量着离家的时光。 山里的月亮总是落得急。还没等我们数清上面的环形山,它就匆匆躲到风车背后去了。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还没酿成语言,就被早班的汽笛声打断。在这片永远转动的白色森林里,我们仰头望见的月亮,永远比记忆中的那个,要冷一些,远一些。 |
|
|
|
| 【打印】 【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