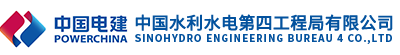【品牌采风】履迹上的东庄 |
|
|
|
|
一脚踩下,归来时鞋底的软泥已半干,竟不忍遽然跺去。这泥土是活的,尚存坝体巨人心脏的搏动,它牢牢咬住皮革的缝隙,像是工程深处递来的无数只黢黑的小手,要向我这过客记者诉说些什么。它比任何采访录音都更真实,是一种原始的证据,黏腻地证明着我曾踏入那个被人力重塑的时空。 东庄的土不是土,简直是活的巨兽蜕下的鳞甲。载重卡车的巨轮碾过,泥浆便如被迫屈服的活物一般向两侧迸溅,旋即又蠕蠕地聚拢,预备吞噬下一批铁兽的蹄足。我的裤管早成了它们的降幡,沉甸甸地垂着,溅满褐黄灰黑的抽象图案,是这大工地慷慨赐予的、无从推拒的勋章。空气弥漫着硝石、柴油与亿万土石方被烈日蒸出的气味,劈面撞来,顽固地附着在喉头,成为一种生理性的记忆,往后几日,我仿佛呼出的仍是东庄的风。 及至抬头,才真真被那景象攫住了咽喉。那大坝自莽苍山峦间蓦地崛起,傲慢地截断了河谷,要将滔滔江河驯作膝下的囚徒。混凝土的崖壁高得令人颈项欲折,上面蠕动着蝼蚁似的车辆与人影,相形之下,深感血肉之躯的渺小与暂存。机器的轰鸣在山谷间反复撞击,回旋,听久了,这声音似是剥夺了人的听觉,重塑了此地的秩序。 我蹒跚前行,泥泞屡次企图剥走我的鞋,仿佛这片土地对一切外来者都怀有固执的敌意。近处,一群工人正与一段扭曲的钢筋搏斗。汗在他们古铜色的脊背上冲出蜿蜒的白色小河,旋即被新涌出的淹没。安全帽下,他们的脸被风霜、烈日和劳碌蚀刻得比山岩更粗糙,唯有一双眼睛,在尘灰的遮蔽下灼灼有光,紧盯手中的活计,那是一种摒绝了一切杂念的、近乎神圣的专注。他们不说话,吼声早被巨大的噪声吞吃了,交流全靠眼神与手势,宛如一群效力于神秘巨灵的哑巴僧侣。他们的辛苦,不是文字里轻飘飘的“挥汗如雨”,而是一种具象的、缓慢的消耗,像水渗入干涸的土地,每一滴都留下印记,却转眼不见,只留下更深的渴。 晌午的烈日将钢铁晒得烫手。我躲进一个临时工棚,里面一位老工程师正对着一张铺开的蓝图,眉头锁得像图纸上等高线最密集处。他用一柄比例尺反复比画,嘴里喃喃着数据,仿佛在念诵祷词。风吹起他花白的鬓角和图纸的一角,他伸手按住,那手背上疤痕与老茧交错,是另一张更复杂、更经磨损的图纸。我递过一瓶水,他接过,道谢,目光却未曾离开那线条与数字的迷宫。我问他这庞然大物何时能驯服脚下的江河。他未即刻回答,啜了一口水,视线越过工棚,投向那不断攀高的水泥巨壁,目光黏涩得如同周遭的泥淖,良久才道:“你看这脚下的泥,我们叫它‘富贵土’,黏上就甩不脱,是命。坝是一寸寸长,人是日头里耗。你鞋上这点,算个啥。”他的话,像一颗石子投入轰鸣的深潭,几乎没激起涟漪,却沉甸甸地坠入我的耳中。 黄昏开始吞噬山谷,巨大的探灯次第亮起,将夜的碎片生生焊在坝体上,勾勒出另一种狰狞而伟岸的轮廓。白班的工人们拖着身影,走向远处的板房,每一步都像从泥里拔出沉重的根。夜班者的吆喝声短暂地划破交接班的片刻寂静,随即又被机器的永恒咆哮淹没。这里没有绝对的黑暗,也没有真正的宁静,这是一场永不落幕的史诗剧。 我终未跺去那泥。它干结在鞋底,成为一种确凿的负累。驱车离开很远,摇下车窗,那混合着尘土、汗水与钢铁的味道似乎仍追随着轮毂。我带回的不是一篇报道的冰冷素材,而是东庄的一小部分肉身,是汗与混凝土的糅合物,是巍峨的另一面,是那些嵌在宏大叙事缝隙里的、缄默的艰辛。那泥土是活着的,时时散发着来自深谷的、潮湿的、正在凝固的庄严,提醒着我另一片时空下,那幅由血肉之躯推动钢铁、以意志对抗重力的壮阔画卷,仍在无声地铺展。 |
|
|
|
| 【打印】 【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