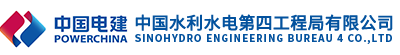若羌的春 |
|
|
|
|
5月的阿尔金山脚下阳光像融化的蜂蜜,均匀地涂抹在塔克拉玛干边缘的戈壁滩上。若羌项目部的板房前,二十棵开春种下的树苗正在经历一场静默的蜕变——灰褐色的枝桠间,嫩芽从树皮裂缝里钻出来,起初只是针尖大的淡青色,十几天功夫就舒展成婴儿手掌般的叶片,在晨风中轻轻翻动,像是春在无声地翻动书页。 综合队的卢队长在早饭前绕着树苗走三圈。他穿旧的工装裤口袋里永远别着软尺,此刻正半蹲着丈量新枝的长度:“新长出的枝桠又窜了三指高。”他说话时喉结在晒黑的脖颈上滚动,唇角沾着没擦干净的粥渍。大家端着鸡蛋包子围过来,饭盒里的小米粥腾起热气,混着新叶散发的清甜气息,在荒芜阴影里织成一层温暖的雾。 项目部门口的小花坛是卢队长和我们的“试验田”。开春时他从县城捎来的多彩向日葵种子,如今已长成手掌高的植株。有几株向日葵都开始顶着鹌鹑蛋大的花盘在风中摇曳了,碧绿色的叶片在风中像一封封未拆的信笺,正等待阳光来书写幸福。最让我们惊喜的是荒漠戈壁的骆驼刺——这些曾经被风沙打磨得只剩枯茎的野生植物,如今在每日清晨的浇灌下,在虬结的枝条上绽满了翡翠色的细叶,叶片边缘的尖刺挂着晨露,在阳光下折射出细碎的虹。 “该给向日葵搭架子了。”司机老罗拿着竹竿经过花坛,锐利的眼睛在花坛上绽放出独有的开心。他同我说话时眼睛盯着向日葵微微弯曲的茎秆,像是在打量需要的物资。晚上夕阳即将落山时,工人们会在树苗下唠嗑,听着叶片在沙沙作响,恍若置身于戈壁深处的绿洲。偶尔有细沙随着热风掠过板房顶,却再不像往年那样一片混沌——新栽的植被像一道绿色的屏风,让肆虐的风沙也变得温柔了些。 在某个宁静的午后,技术员小李正在办公室里整理图纸,忽然看见窗玻璃上投下几个晃动的黑点——是苍蝇,比内地常见的品种略小,翅膀透明得能看见细密的纹路。它们停在窗户外晾晒的衣服上,细长的口器在被单里不知道探寻着什么秘密。傍晚打饭时,蚊子的嗡鸣加入了戈壁的春景,起初只是零星的高音,很快变成成片的低音炮,在大家耳旁挥之不去。 “要是有艾草,把艾草挂在门框上就好了。”小徐望着大门外随风摆动的树叶突然来了主意,转身从空地处折了几枝半枯的骆驼刺枝条。深褐色的枝干上还带着去年的尖刺,鲜嫩的绿叶被揉碎时竟散出清凉气息,混着沙土的干燥味道在空气中浮动,倒比想象中更添了几分戈壁特有的清爽。 安全员小吴蹲在地上往窗缝隙里填发泡胶,鼻尖沁着细汗:“这些小东西比我穿针还难缠。”他指尖捏着从发泡胶筒,突然瞥见纱窗外侧停着只灰蛾——翅膀半透明的灰白色,边缘染着淡淡的金,正静静伏在自己种的蓝莓草边缘,细长的足尖陷进花芯的绒毛里。他举着灭蚊拍的手悬在半空,看那蛾翅随着枝桠的晃动轻轻起伏,像片被风托住的银杏叶,最终慢慢放回了窗台。 夜晚的项目部有了新的声音。大型机械的轰鸣不再是唯一的背景音,飞蛾撞击顶灯的“哒哒”声、苍蝇在纱窗上爬行的“沙沙”声,与远处阿尔金山传来的夜风呼啸交织在一起。喜欢夜间出去散步的我们在树苗旁用手电筒的光束偶尔掠过叶片,会看见细小的小虫子在叶脉处滚落,惊醒趴在叶背的小黑虫,它鞘翅展开时闪过的金属光泽,像极了阿尔金山上落日余晖下的矿石。 最动人的时刻出现在黎明前。启明星还挂在阿尔金山尖时,卢队已经提着水桶出门了。新抽的枝条在微光中泛着银青色,叶片上的绒毛沾满细沙,水珠落在沙粒上溅起小小的雾。他浇水时总把水流放得很慢,看清水在沙土表面蜿蜒出细小的沟渠,看每片叶子都痛快地舒展身躯,想要听见根系在地下咕嘟咕嘟喝水的声音。 风沙依然会来。某个黄昏,天边突然涌起铅灰色的云,细沙随着狂风拍打板房的铁皮,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工人们依旧冲在一线努力奋斗,塑料布在风中猎猎作响,却没人注意到自己的工装早已沾满沙粒。当风沙过后,他们看见向日葵虽然暂时垂下了花盘,却在次日清晨重新昂起头颅,叶片上的沙粒被露水冲刷得干干净净,像是从未经历过这场劫难。 如今的项目部门口,二十棵树苗已连成小小的林带。正午时分,阳光穿过叶片在地上织出斑驳的网,工人们走过时会故意踩一踩那些晃动的光斑,给生活增添了无限乐趣。苍蝇蚊子依旧在周围盘旋,却成了这幅生机画卷里不可或缺的点缀——就像戈壁滩不会只有晴朗,却因为这些生命的存在,让每一粒风沙都有了温柔的理由。 深夜,总有人坐在板房前的台阶上,他们能看见新叶在夜风中轻轻摇晃,听见远处钢筋碰撞声踏过沙丘。这是属于戈壁的浪漫:没有繁花似锦,没有莺歌燕舞,却有最顽强的生命在滚烫的沙土里扎根,有最朴素的喜悦在粗粝的生活中生长。当第一颗露珠落在新抽的嫩芽上,当第一只飞蛾扑向光明的灯盏,这片曾经被认为不可能有春天的土地,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展现着关于生命与希望的故事。 |
|
|
|
| 【打印】 【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