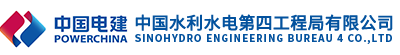汗水与秋意的交响曲 |
|
|
|
|
在广西来宾抽水蓄能电站的工地上,晨露在钢筋架上凝成细小的冰晶时,老李正弯腰系紧劳保鞋的鞋带。塔吊的长臂划破鱼肚白的天际,他忽然发现今天的风里少了些灼人的棱角——原来立秋已至。脚手架上还残留着昨夜的潮气,指尖触到钢管时不再是盛夏那种烫手的温热,倒像触到了井台边沁凉的石板。 他往手心啐了口唾沫,抓起扳手开始紧固螺栓。东边的塔吊正在吊装钢筋,铁链摩擦的哗啦声里,混进几声清脆的鸟鸣。老李抬头望了望,看见两只麻雀在塔吊臂上跳来跳去,啄食着不知哪个工人掉落的馒头渣。这要是在七月,鸟儿早躲进树荫里避暑了,哪会像现在这样在日头底下撒欢。 搅拌机的轰鸣声里混进了秋虫的唧鸣,这是工地最微妙的换季信号。老张推着灰斗车经过料场时,裤脚扫过堆成小山的砂石,惊起一片细碎的尘土。他习惯性地用手背贴了贴灰桶边缘,混凝土的温度比昨日降了三度,这细微的变化逃不过他在工地摸爬滚打三十年的手掌。 忽然想起老家院角的梧桐树该落第一片叶子了。去年此时,他蹲在灶台前烧火,老爸正把新摘的秋葵切成小段,窗外飘来的梧桐叶落在案板上,带着清清爽爽的秋味。他抹了把脸,汗珠坠在下巴尖上,没像盛夏那样连成线,反倒被穿堂风卷着打了个旋儿,落在满是裂纹的水泥地上,瞬间洇出个深色的圆点。 钢筋班组的后生们光着膀子绑扎箍筋,古铜色的脊梁上汗珠滚滚,却没人像七月那样张嘴直喘。小王把最后一根扎丝拧成麻花状,直起身时腰骨发出轻微的咔嗒声。他从工具箱里翻出件薄外套,蓝布面上还沾着上周浇筑时溅的水泥点子。 “这会儿就穿衣裳?”蹲在旁边调直钢筋的王师傅笑他,“等会儿太阳上来,保管你脱得比谁都快。” 小王嘿嘿笑着把外套搭在肩膀上:“师傅您看,影子都变长了。”他伸直胳膊,指尖的影子在地面上拉得老长。七月的日头正毒时,影子都缩成一团贴在脚边,哪像现在这样舒展。 正午的太阳依旧把安全帽晒得发烫,但阴影里已有了凉意。伙房的大师傅推着餐车过来时,铁桶里的绿豆汤还冒着热气,却不再像伏天那样让人望而生畏。老李捧着粗瓷大碗蹲在临时工棚外,看见远处塔吊司机探出半个身子换衣服,蓝色工装袖口沾着的白灰被风扫下来,像极了老家屋顶飘落的炊烟。 七月的夜晚像个密不透风的蒸笼,就算歇着也浑身淌汗,哪敢奢望加班。老李望着堆在不远处的预制板,板面上凝结的水珠还没被晒干,在阳光下亮晶晶的,倒像是谁撒了把碎玻璃。 料场的帆布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卷着几粒金黄的杨树叶掠过脚边。保管员赵姐正拿着台账核对钢筋数量,手指划过冰冷的铁材时,忽然发现锈蚀的速度好像慢了。伏天里的钢筋搁三天就锈迹斑斑,现在摸上去还是硬硬的质感。她弯腰捡起一片被风吹来的梧桐叶,叶边已经泛黄,脉络却还清清楚楚,像谁在上面画了幅细巧的地图。 “赵姐,给我捆扎丝。”小王抱着钢筋跑过来,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落在锁骨窝里却没继续往下流。“这天真是变了,早上来的时候,自行车座上都挂着露水。” 赵姐低头在本子上划着记号,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里,能听见远处传来的锤击声,咚、咚、咚,比盛夏时的节奏慢了些,却更显沉稳。她想起今早路过家属院,看见张师傅的媳妇在晾被子,被单在绳子上晃晃悠悠,不像伏天那样沉甸甸的,倒像是能随风飞起来。 暮色来得比上个月早了一刻钟。当最后一车砂浆卸完时,西天正铺着火烧云。几个工人坐在钢管堆上抽烟,烟圈刚飘起来就被秋风扯散。有人说该给家里寄秋衣了,有人念叨着中秋的工期能不能赶完,烟蒂在地上明灭,映着他们被夕阳拉长的影子,像一排沉默的钢筋。 “我家小子昨天打电话,说学校要秋游了。”电工老刘磕了磕烟灰,“去年这时候还在工地上跟着我吃泡面呢。” 老李摸出藏在裤兜里的皱巴巴信纸,是上周闺女寄来的,说家里的玉米快熟了,等收完秋就来工地看他。信纸边缘已经磨得起了毛,他却还能闻到上面淡淡的玉米香。 夜露开始在跳板上凝结时,工地的灯次第亮起。塔吊的探照灯扫过正在绑扎的钢筋网,在地面上投下纵横交错的影子。搅拌机停止转动的间隙,能听见蟋蟀在地基深处唱歌,唧唧、唧唧,比盛夏时的叫声更清亮。 老李裹紧外套往宿舍走,路过材料堆时,看见几只蜗牛正趴在防雨布上慢慢爬。伏天里哪见得着这东西,早被晒成了空壳。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在乡下,立秋那天总要跟着大人去田埂上找蜗牛,说吃了能治尿床。那时候的秋风也是这样,吹在脸上凉丝丝的,带着稻穗的香气。 宿舍的灯泡忽明忽暗,老张正用铁丝捆着行李:“我跟队长请假了,下礼拜回去收秋。”他的铺底下塞着双新布鞋,鞋面上绣着一朵小小的菊花,是媳妇前阵子寄来的。“你们谁要带东西,趁早说。” 老李摸了摸枕头底下的钱袋子,里面的票子已经攒得差不多了,够给孙子买台学习机。窗外的风卷着落叶打在玻璃上,沙沙作响,像谁在窗外轻声说话。他想起老家的炕头,这时候该烧起来了,暖烘烘的,能把一身的乏气都烤出去。 远处的拌合站传来机器启动的声响,夜班开始了。老李躺下来时,听见隔壁床的小王在翻身,嘴里嘟囔着什么,大概是梦见家里的秋收了。月光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在水泥地上画出细长的线条,像谁在地上拉了根银线。 他忽然想起早晨系鞋带时,看见鞋跟沾着的泥块里,裹着半片干枯的花瓣。大概是从哪个墙角的野花上粘来的,在盛夏的烈日里没被烤成灰,反倒跟着他挨过了三伏,迎来了这带着凉意的立秋。 |
|
|
|
| 【打印】 【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