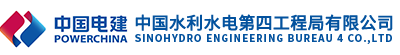风吹过旷野,变成了明亮的灯 |
|
|
|
|
小时候,我是顶憎恶那些塔筒的。 它们不知何时,便如雨后林间的菌子,一夜间占满了远近的山梁。白的,直挺挺的,冷冷地立着,像一群闯入故园的不速之客。白日的喧嚣尚可忍受,到了夜里,万籁俱寂,那风叶搅动空气的呜呜声,便格外清晰地漫进窗来。那声音,不似夏蝉的聒噪,也不似野狗的狂吠,倒像是一个固执的巨人在旷野上低咽,呜哩呜哩的,搅得人心烦。我用被蒙了头,那声音却仿佛能穿透墙壁,直钻进耳膜里来。我便想,这烦人的东西,平白夺了山野的静谧,扰了人的清梦,实在是可恨的。 后来年岁渐长,离了那山村,到城里工作生活。见过许多热闹,也听过比那风鸣更刺耳的声响,旧时的厌恶,便也淡了。可命运使然,我竟进了制造那“铁筒”的工厂。 于是,我的天地便不同了。眼前不再是青绿的山,而是钢铁的丛林;耳畔不再是低咽的风鸣,而是震耳欲聋的锤击与焊接的嘶吼。我亲手抚过那冰凉的钢板,看着它们如何在火焰与汗水里弯曲、连接,一节一节,垒成那庞然的巨物。我才知道,那令我童年失眠的呜咽声,须得经过这般千锤百炼,才能发于天际。 旧时最高的,怕是庙里的塔,皇家的宫阙。那塔是用来镇妖的,带着法海禅师一般的冷脸,教人仰视,也教人窒息;那宫阙是显着威严的,朱红的墙隔开了内外,教人敬畏,却不敢亲近。 而今,这白色的巨筒,却兀自立在四野了。它不像塔那般藏着精怪的传说,也不像宫阙那般摆着帝王的架子。它只是站着,简简单单,坦坦荡荡,用一身素白,对着苍天与黄土。 有人说它孤直,像愣头愣脑的呆子。但它这呆,却是一种诚实的呆。它不言语,不标榜,只将那旷野里无人收管、徒然吹散了茅屋的野风,一把揽住,化作一股实实在在的力。这力,不再是催花折木的暴虐,而是点亮一室灯火,转动万家轮轴的根基。 先前,我们靠煤。那地底挖出的黑金,固然有力,却也沾着矿工的血与汗,冒着熏黑了天日的浓烟。如今这巨筒,吞进去的是天地间无用的长风,吐出来的,却是清清白白的“光明”。这便如一个沉默的巨匠,将无用的,化为有用的;将虚妄的,变为实在的。于无声处,竟做着这般改天换地的事业。 在夜里,它顶上的红灯一亮一灭,像是一只清醒的眼。这眼不窥人隐私,只望着茫茫暗夜,为迷途的飞鸟指点方向。那巨大的影子在地上移动,也不再是压迫的影子,倒像一个巨大的时辰钟的指针,在丈量着这土地走向新生的脚步。 我于是想,这便是一种新的“中国的脊梁”了。它不像古塔,代表着压人的旧物;它是一座新塔,骨子里是铁,是钢,是求实的学问与坚韧的毅力。它不必藏在深山里,它就站在人人看得见的旷野上,告诉人们:“看罢,我们也能造出这样不骗人的、有用的东西了!” 我站在竣工的塔筒下,仰头望去。它通体雪白,直插云霄,巨大的叶片在风中缓缓旋转,划开流云。那一刻,我竟失了神。那曾经恼人的噪音,此刻听来,却像是一曲浑厚的歌。它唱的,不再是山野的幽怨,而是将散漫的风,收束为力,将虚妄的自然,化作照亮人间一隅实实在在的光明。这漫山遍野的,不再是侵略者,倒像是缄默的卫兵,用它们钢铁的脊梁,扛着这沉重的天空,也扛着一个时代向前去的指望。 我看着那些白色的巨筒,一根根地立在旷野上、山脊间,像是从地底长出的嶙峋的骨,又像是巨人遗下的沉默的杵。它们就这样站着,一言不发,只管向着天。人们说,这是好东西。能生出电,驱了煤的黑烟,带来些所谓“清洁”的光明。于是便有许多人称赞,仿佛立了这巨筒,天地间便顿时干净了起来,前程也一片光明了。同样的风,在山野间是散漫无用的,甚或能成灾;入了这塔筒,却成了驱散黑暗的根基。看来,事物本无定性,全在人之所为。那吵我睡觉的,与这今日令我敬畏的,原是同一物。变的不是塔筒,是塔筒下的人的心境了。 我于是恍然大悟,感到一种深深的惭愧。先前的憎恶,原是我的肤浅。正如闰土只知香炉和烛台是物件,却不知其为何用;我当年也只听见了噪音,却未曾想过这噪音里头,竟藏着这般雄浑的力量。 我无法如赞美雷霆日月那般赞美它,因它本是人的造物。但我却愿为这沉默的、实干的塔筒写几个字,只因在它的影子里,我似乎看见了一点中国的筋骨,和一点未来的、踏实的光明。 |
|
|
|
| 【打印】 【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