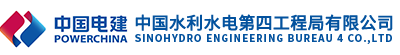麦香里的乡愁 |
|
|
|
|
立夏的日头在钢筋水泥间打了个转,落进搅拌机的轰鸣里。我摘下安全帽,任暖风撩起鬓角汗湿的发梢。远处麦田正翻涌着青黄相接的浪,恍惚间竟与记忆里川南的竹海叠在一处了。 龙门吊的钢臂切开五月的云絮时,豫中平原的麦子正在抽最后一道浆,豫中平原的夏是蘸着麦浆长起来的。晨光漫过制梁场蓝白相间的围挡,在绑扎成网的钢筋上溅起细碎银星。在这大好晨光里,麦穗们垂首私语,将青涩的锋芒藏进渐染金边的叶鞘。农人蹲在地头,掐一穗麦粒嚼出浆来,便知该往田埂上再浇一茬水。他们黝黑的面庞总让我想起父亲,在甜城郊外的荷塘边,他弯腰采藕时溅起的泥点,也是这样在皱纹里开出花来。 故乡的立夏总要落几场急雨的。沱江裹着新涨的春水,在青石码头撞碎成千万朵银花。这时节内江的竹林最是喧闹,笋尖顶开腐叶的刹那,满山都是竹节拔高的脆响。母亲总要在檐下煨一罐老荫茶,说是喝了能祛除湿气,其实是为着让茶香牵住过路的风,捎来江面货船悠长的汽笛。 此刻制梁场里,龙门吊正将百吨重的箱梁稳稳托起。混凝土在模具中凝固成流动的岁月,钢筋编织的经纬里,分明能触摸到中原大地的脉动。来自商丘的钢筋工老张笑说等麦子黄透时,咱们架起的桥墩就能托着列车,在金色的海洋上划出银亮的航线。我望着天车划过晴空的轨迹,忽然听见熟悉的川音在麦浪里轻轻摇晃——那是千里之外的竹林,正把晨露酿成月台上相逢的泪光。 暮色漫过测量仪的红外线时,手机屏突然亮起母亲发来的照片:老屋门前的枇杷树缀满金果,父亲站在竹梯上,手里捧着的何止是初夏的馈赠。我转身望向正在浇筑的桥墩,钢筋混凝土的骨骼里,生长着比麦芒更坚韧的守望。或许当高铁贯通南北那天,蜀道的云雾与中原的麦香,会在飞驰的车窗里酿成同一杯乡愁。 河南的立夏是土地与烈日对酌的酒盏。农人把裤管卷过膝盖,赤脚踩进晒得温热的田埂。麦芒扫过他们古铜色的小腿,在皮肤上划出金黄的符咒,像是给即将出征的勇士纹身。隔壁农民工宿舍的老李头总爱蹲在预制梁边吃午饭,搪瓷缸里浮着油花的胡辣汤,总让我想起母亲用醪糟煮的荷包蛋。我和他相识于宣传工作中的偶然,他教我用麦秆编蝈蝈笼,粗粝的指节翻飞如梭,麦香便顺着经纬流淌成河:“等高铁通了,让四川的幺妹儿坐着动车来收麦。” 甜城的立夏却总浸在沱江的雾气里。晨起推窗,湿漉漉的竹梢扫过黛瓦,将昨夜新发的笋香抖落在青石板上。父亲常在天井里支起竹匾晒盐花生,说是要备着梅雨季下酒。我最爱偷掀蒸笼,看艾草染绿的立夏粑如何在蒸汽里舒展腰肢,糯米香缠着花椒叶的辛烈,像极了蜀绣娘手中交织的彩线。檐角铜铃响时,货船正载着甘蔗顺流而下,艄公的号子撞碎在张大千纪念馆的粉墙上,惊起一群白鹭掠过圣水寺的飞檐。 此刻制梁场的震动台正在轰鸣,混凝土顺着导管注入钢筋编织的摇篮。我望着梁场里整齐列队的箱梁,恍惚看见故乡的龙舟正划过端午的江面。我忽然想起内江糖厂的青砖老墙,那些在岁月里结晶的糖霜,是否也如同此刻凝固的水泥,将甜蜜与坚硬糅成岁月的骨骼。 暮色染红起重机的刻度时,手机里跳出母亲发来的视频。老宅后的荷塘新添了十亩,父亲穿着雨靴在藕田里蹚水,惊起的蛙群跃过镜头,把川南的梅雨溅进中原的晚霞。画面忽然摇晃起来,原来是小侄女举着手机追拍白鹭,稚嫩的川音裹着枇杷香:“嬢嬢你看,鸟儿翅膀上挂着彩虹!” 夜色中的制梁场亮起星辰般的照明灯,龙门吊在月光里划出银色轨迹。我知道此刻在沱江两岸,萤火虫正提着灯笼掠过甘蔗田,而中原的麦茬地里,蟋蟀开始吟唱秋收的序曲。当明天的太阳跃出地平线,这片浇筑着汗水与思念的土地上,所有等待破土的梦都将在钢轨的震颤中,找到归乡的韵脚。或许每条钢轨都是大地伸向远方的叶脉,而我们的乡愁,终将在某个飞驰的黄昏,被麦浪与竹海共同托举成地平线上温柔的弧度。 |
|
|
|
| 【打印】 【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