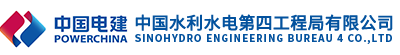我与父亲在工地的春天 |
|
|
|
|
一场春雨悄然而至,细密的雨丝浸润着沉睡的大地。项目部前的老垂柳最先感知春意,枯竭的枝桠上缀满鹅黄新芽,随风轻颤时宛若流动的绿烟。远处的溪水裹着碎冰叮咚作响,偶尔有银鳞跃出水面,溅起的水花在阳光下折射出碎钻般的光泽。潮湿的泥土气息混着草木清香扑面而来,恍惚间,记忆如抽芽的藤蔓攀上心头——那是二十年前,我与父亲在工地的春天。 父亲是塔吊司机,常年辗转于荒山野岭的工程间。每年惊蛰前后,母亲总会拎着腌好的腊肉和晒干的野菌,牵着我的手翻过两道山梁去探亲。项目部用彩钢板搭了两间探亲房,墙缝里塞着旧棉絮御寒,铁架床上铺着洗褪色的蓝格床单。那时只觉得新奇,如今回想,斑驳墙面上用粉笔画的小人、窗台上半瓶野花干、门后挂着沾满泥浆的旧工装,皆是粗粝岁月里最温柔的注脚。 记得某个雨日,父亲难得休工,和工友蹲在屋檐下聊天。雨滴顺着铁皮檐角连成珠帘,我在起雾的玻璃上画飞机,机身歪斜地穿透云层,尾迹掠过父亲泛白的鬓角。他们聊着汛期前要抢完浇筑量,混着雨水敲打铁皮的声音,竟谱成一首安眠曲。那幅画面,至今仍在记忆深处泛着毛茸茸的暖光。 父亲总说春天是塔吊司机的节日。驾驶室悬在百米高空,推窗便能拥满湿润的春风。返青的山峦像打翻的翡翠匣子,吊臂上的麻雀啄食他偷偷撒的小米,羽翼扑棱时掀起细碎的金色尘埃。最震撼是遇见北归的雁阵,澄澈天幕下,“领头雁”的啼鸣穿透钢铁丛林,灰白羽翼掠过操纵杆的瞬间,父亲说能听见山河苏醒的轰鸣。 而今我站在调压井旁,安全帽檐凝着晨露。钢筋丛林里,春风仍裹挟着熟悉的焊花气息。那只总在食堂偷馒头花的狸花猫,正追着蝴蝶闯进混凝土养护棚;藏族工友扎西的经幡挂在通风洞口,五彩布条与山桃花纠缠飞舞。我举起相机对准正在绑扎钢筋的王师傅——五十岁的老工程人半跪在基坑,布满老茧的手将铁丝拧成蝴蝶结,身后野油菜花开成一片海。 黄昏时收到父亲视频,他正在老家院中修剪石榴树。“塔吊上的春天看够了,现在要守着自家一亩三分地。”镜头忽然摇晃,母亲端着青团入画,蒸腾的热气模糊了屏幕。我转身望向项目部,落日为龙门吊镀上金边,更远处,雪水融成的溪流正奔向初具雏形的大坝。 这个春天,我的笔记本里夹着一枝野杏花,花瓣上还沾着洞壁渗出的山泉水。当第一方混凝土注入基岩时,山风忽然转暖,恍惚听见父亲当年描述的雁鸣——那声音穿过二十年光阴,落在测温仪的显示屏上,化作跳动的数字,续写着新的春天史诗。 |
|
|
|
| 【打印】 【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