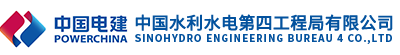墨里廉风,乌溪为证 |
|
|
|
|
午后的阳光斜斜浸进办公室窗棂,落在摊开的宣纸上,晕出一片暖软的光。我正捻着狼毫蘸墨,忽然听见窗外乌溪江的风,裹着水汽掠过檐下的竹帘——那风是带着江的味道的,湿凉、清透,像刚洗过的棉麻,裹着远山的青气,往纸页上扑。 索性提笔,顺着这风的性子落字:先写“风”,笔锋斜掠出去时,竟像跟着林梢的枝桠晃了晃,墨色里都裹着江风穿过松针的轻响,连烟火气都被吹得淡了;再写“清”,蘸墨时特意兑了点凉茶水,一笔下去,墨痕在宣纸上洇开的纹理,像极了江心石缝里渗出来的泉,清得能看见水底的苔衣;轮到“气”字,手腕不自觉沉了沉,笔锋顿在纸间时,忽然想起清晨在项目工地见的景象——技术员蹲在钢筋堆旁校量尺寸,安全帽檐的露水滴在图纸上,晕开的墨线也是这样挺括、端正;最后落“廉”,特意把笔锋按得实了些,墨色沉在纸里,像江底浸了百年的石,不浮、不飘,稳稳立着,连纸页都似多了几分分量。 搁笔时指尖还沾着墨香,抬眼望出去,乌溪江正绕着项目营地的山坳蜿蜒——江面上有采砂船慢悠悠驶过,浪痕在阳光下铺成细碎的银,却没搅乱水的澄明;远处的桥墩正往云里长,钢筋的冷硬裹着混凝土的温,和江风撞在一处,竟揉出了踏实的暖。 正想着,旁边张瑶衣袋里的对讲机忽然响了:“物资部张工,下午的砂石料进场,过磅数比清单差了两吨,麻烦过来复核下。”攥着对讲机往工地走,鞋跟踩在碎石路上,硌得脚掌发沉——这沉,像极了刚才写“廉”字时按下去的笔锋。到料场时,收料员正蹲在磅秤旁翻单据,砂石堆旁的标尺还沾着湿土,他指尖在数字上划了两道,抬头笑:“张工你看,供应商说潮料压秤,咱按干料折算,这数得抠准。”风裹着砂粒吹在脸上,我忽然想起宣纸上的“清”字——原来这“清”,不只是江泉的澄,更是算料时不肯含糊的那道小数点,是指尖划过单据时,印在纸上的实诚。 于我们四局人而言,这纸上的墨从不是闲笔:风清,是蹲在基坑边核对数据时,心里没杂尘的静;气正,是捧着图纸和协作队伍交底时,话里没含糊的直;而这“廉”字,早成了踩在工地上的脚印——是材料过磅时多核对的那组数字,是收方计量时俯下身量的那道标尺,是乌溪江水漫过脚踝时,浸在骨子里的干净。 日头渐渐偏了,江风又起,吹得宣纸上的墨痕微微泛着润光。我把写好的字立在窗边,忽然觉出这字与这江的缘分:乌溪的水是干净的,清得能映见云的模样;我们笔下的字是扎实的,沉得能接住脚下的土——原来从墨里到工地上,从江风到人心,“干净”与“扎实”,本就是揉在一处的。 |
|
|
|
| 【打印】 【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