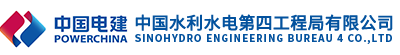风过如晤 |
|
|
|
|
风,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穿行,总带着一种属于奋斗者的独特气息。它拂过塔吊高悬的长臂发出轻微的嗡鸣,在成捆钢筋的棱角上打着旋儿,又顺着脚手架的缝隙,悄然潜入尚未封顶的楼宇骨架深处——这气息是四局人刻入骨血的印记,混合着新拌混凝土的微腥、钢铁锈蚀的淡淡苦涩,以及日头长久曝晒下模板木料的干燥暖香。 初识风的语言,是在米东项目的那个初夏。正午的日头毒辣,将头顶的安全帽炙烤得滚烫。我跟随技术办的李主任去拍摄基坑支护,脚下是深陷的土地。忽地一阵风卷着沙砾滚过,吹得图纸猎猎作响。李主任抬手按住图纸,指尖在钢筋标注上轻轻点了点,眯眼望向坑底那片排列如林的钢筋网格,笑道:“听见没?这是地基在跟咱打招呼呢。”他侧耳倾听风穿过钢筋间隙发出的、细密而悠长的嗡鸣。 自此,我渐渐开始停下来去听听风的低语。晨曦刚漫过围挡时,风裹着薄薄的清润水汽,掠过覆盖严实的建材堆场,那低柔的沙沙声,是它提醒我们检查昨夜苫盖是否妥帖的絮语;烈日当空的正午,风裹挟着灼人的热浪,猛烈撞击在绿色的防护网上,发出沉闷的、持续不断的呼呼声,像焦灼的催促,提醒人们暂避锋芒;待到暮色四合,风便穿梭于初具雏形的墙体间,在预留的管道孔洞中打着旋儿,那呜咽般的哨音里,分明藏着对楼宇封顶、尘埃落定的深切期盼,还有对万家灯火的向往。 记忆里最凛冽的风声,是2023隆冬抢工期的日子。北风卷着细密的雪粒子,像无数冰冷的鞭子,狠狠抽打在临时板房的铁皮屋顶上,整夜整夜地呜呜哭嚎。下午五点,寒气已刺透身上的棉衣,从办公楼往外望去是一片几乎吞噬万物的苍白。远远地,在塔吊投下的浓重阴影里,瞥见钢筋工刘师傅佝偻的身影。他蹲在地上绑扎箍筋,棉手套被铁丝勾出好几个破洞,露出的指尖冻得通红。忽然吹来一阵疾风猛地掀起他陈旧的安全帽檐,刹那间,鬓角凝结的白霜簌簌往下掉。“这风啊,”他搓着冻得通红的、几乎失去知觉的手,声音在风里显得嘶哑,“是想试试咱这把老骨头,到底还硬不硬气。”那天的风确实凶悍,吹得人几乎站立不稳,摇摇欲坠。然而,当清晨第一缕金色的阳光,终于艰难地穿透阴霾,温柔地铺洒在我们一排排厂房上时,肆虐了一夜的风,竟奇迹般地缓和下来,轻柔地拂过钢梁,连平日里泛着冷光的厂房也在那一瞬间看起来柔和。 最令人心潮澎湃的风,属于办公楼封顶那一刻。庞大的起重机吊着最后一块预制楼板,在所有人的屏息凝望中,极其缓慢又无比坚定地升向高空。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喧嚣的工地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风,骤然停了。连空气中原本躁动飞舞的尘埃,都仿佛失去了依托,静悄悄地落回地面。整个世界只剩下那庞然大物上升的轨迹。直到楼板严丝合缝地嵌入预留的卡槽,焊工手中的焊枪在半空骤然迸射出璀璨耀眼的蓝色火花,像一朵瞬间怒放的金菊——风,才仿佛重新获得了生命,带着所有人积蓄已久的、火山爆发般的欢呼声浪,奔腾着、雀跃着穿过一层层新生的楼层。那一刻,风的味道复杂而浓烈:是汗水浸透工装后挥发的咸涩,是水泥粉尘沾染皮肤的干燥苦味,更是无数双眼睛因激动而闪烁的、足以点亮黑夜的光芒。我独自站在楼顶边缘,看风追逐着远处塔吊的剪影,将庆祝的彩色飘带和气球高高托起,送入辽阔的晴空。就在那一瞬间,我彻悟:四局人与风的每一次相遇,从来都不是擦肩而过,而是一场彼此见证、彼此成就的双向奔赴。 如今,每每路过那些经由我们双手拔地而起的厂房、办公楼,我都会习惯性地驻足片刻,侧耳倾听风的脚步。当它穿过光洁的玻璃幕墙,发出清越而悠长的回响,那是在转述千家万户窗内锅碗瓢盆的碰撞,诉说寻常日子的安稳与丰饶;当它轻拂过道路两旁新植的绿篱,带来叶片相互摩挲的细碎沙沙声,那是在低吟光阴静好的诗篇。而那些深深镌刻在建筑肌理深处的风痕——是脚手架搭扣被风沙经年累月打磨出的光滑圆润,是预埋件表面在风尘洗礼下泛出的温润光泽,是岁月之风在外墙面上悄然蚀刻出的、如同年轮般的细腻纹理晕开淡淡的光泽——都是时光老人亲笔写下的、沉甸甸的回信。 风过无痕?不,它在四局人的生命年轮里,早已刻下无法磨灭的印记。它记得每一根钢筋在冷弯时倔强的姿态,记得每一方混凝土在凝固时深沉的缄默,记得每一个深更半夜里,为抢进度而彻夜不熄、如同星辰般点缀在庞大黑影中的灯火。当我们终于站在自己亲手浇筑、亲手垒砌的土地上,听风穿过层层叠叠的岁月之墙,那感觉,恍若与无数个曾经的自己猝然相逢——烈日下汗水滚落砸进泥土的清晨,暴雨中肩扛沙袋奋力堵漏的深夜,为了图纸上一毫一厘的精确而争得面红耳赤的瞬间……所有奋斗的剪影,所有坚守的棱角,都在穿堂而过的风里,清晰重现。 这,大概就是四局人与风之间永恒的默契约定:我们以双手和汗水,在大地的画布上重塑山河的轮廓;风,则以它永不停息的流动,忠实地记录下我们每一步跋涉的足迹。每一阵掠过繁忙工地的风,都是一次久别重逢的晤面。它问候着那些浸透汗水的白昼,抚慰着那些灯火通明的长夜,并最终,将最深沉的祝福,送给那些由我们亲手孕育、即将诞生的崭新风景。 |
|
|
|
| 【打印】 【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