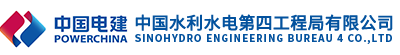离乡千里处,大坝正年轻 |
|
|
|
|
列车终究是在西安站吐出了我们这一群人。二十二人,像二十二粒被命运攥紧又忽然撒开的豆子,骨碌碌地滚到这陌生的站台上。站台是阔大的,喧哗是鼎沸的,各色的声响与气味,热烘烘地扑上来,却又隔着一层,仿佛我们是隔着毛玻璃看这人世。来接我们的是一辆中巴车,引擎声粗重而诚恳,像一头喘着气的铁兽,将我们和塞得鼓鼓囊囊的行李,一同囫囵吞进了肚里。 车驶离了那灯火通明的庞然大物,一头扎进渐浓的夜色里。先是街灯,一排排地过去,像疲倦的、眨着的眼;后来便是连片的黑了,只有车灯劈开的一小截路,惶惶地亮着,随即又被黑暗吞没。喧哗是早就没有了,连犬吠也稀罕,只有车轮碾压地面的单调声响,和窗外那沉甸甸、无边无际的静。静得人心里发空,发慌。有人低声说着什么,话一出口,便被这静稀释了,飘散开,寻不着踪迹。这“争气”的前路,怕不是一口深不见底的井?我们正往那井的深处坠去吧。 然而目的地却并非一口枯井。 车拐过一个山坳,蓦地,一片惊人的“热闹”劈面撞来!那不是人声的鼎沸,是光的、声的、力的交响!远处的山体被探照灯切成巨大的、明暗交错的剖面,煌煌然如同自地底升起的殿宇。一道道缆索横跨深谷,上面缀着的灯点,是凝固的、飞驰的星。最撼人心魄的是那机器的轰鸣,并不尖利,而是沉浑的、连绵的,从大地的深处涌上来,仿佛这山体本身在呼吸,在低吼。间或有哨声、有隐约的号子,峭厉地穿透这轰响,像闪电划开层云。我们一个个扒在车窗上,鼻尖抵着冰凉的玻璃,方才那点凄惶的不安,竟被这洪荒伟力般的景象震得碎碎的,散入夜风里去了。原来,这寂寥的群山深处,藏着一个如此滚烫的、搏动着的世界。 我们这一群“豆子”,便在这“世界”里落了土。起初的一个月,便只做一件事:看,听,嗅,触摸这座正在生长的大坝。白日里,我们追着前辈们的脚印,在基坑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仰头看那钢筋的丛林如何拔节;夜里,便聚在板房,围着图纸与模型,听那些黝黑脸庞上的眼睛,如何亮晶晶地讲述“约束”“应力”“温控”。大坝之于我们,不再是新闻里遥远的名词,它有了体温,有了脉搏,有了每一条仓号独特的脾性。 很快,二十二粒豆子,便被撒向了不同的土壤。 云南来的小穆,分在了质量管理部。他手里常攥着一支长长的温度计,不像医生,倒像个固执的测字先生。他的世界,便是大坝混凝土的“体温”。骄阳似火时,他担心它“烧”着了;寒夜料峭时,他又怕它“凉”着了。他的手抚过那些新浇的仓面,神情专注得像在聆听婴孩的呼吸。他说,这坝体的“病”,都是从一丝一毫的温度差上起的。于是,白日黑夜,他都在与这沉默的巨物进行着一场关乎“健康”的、无声的对话。 同是云南来的小杨,则在工程技术部与图纸和钢筋料表“斗智斗勇”。她的案头,图纸堆得能淹没人。她总蹙着眉,用笔尖在那密麻的线条与数字间游走,搜寻着毫厘的差池。她说,那一根根钢筋,不是冷铁,是大坝的筋骨;那一张张料表,不是废纸,是筋骨生长的图谱。错一个数,筋骨便可能错了位。她的战场没有硝烟,却关乎全局的成败。她伏案的背影,常让我想起雕版的匠人,每一笔,都力透纸背,刻下的便是千秋的印记。 山西的小王,管的是物资设备,他自称是押运“粮草”的。从巨大的缆机配件,到一枚不起眼的螺丝,都在他的账本上活着,呼吸着。他的电话总是最忙的,在山风里扯着嗓子喊,协调着车与船,计算着时间与损耗。他说,这工地像一头巨兽,每日要吞下成山的“粮草”,他的活儿,就是不能让这巨兽饿着,也不能让它“消化不良”。风吹日晒,他的脸很快便与老工人们成了一色,只是眼神里,还跳跃着一种精于筹算的亮光。 至于我,河南的小彭,留在了综合管理部。我的“战场”在文字与影像里,在党群活动的细密组织中。我试图用笔与镜头,去捕捉那些奔流的汗,那些专注的眼,那些深藏的笑与泪。我记录下技术讨论会上激烈的交锋,也记下班组饭堂里辛辣的玩笑。我深知,我所描绘的,不过是这宏大叙事里极细的一笔,但这一笔,须得真诚,须得滚烫。 天南海北的口音,在这山坳里碰撞、交融。云南的菌子,山西的醋,河南的胡辣汤……乡愁化作了舌尖上的滋味,在职工食堂里分享,便成了抵御漫长日夜的一点暖意。我们迎着峡谷里第一缕挣脱山巅的朝阳走上工地,又披着漫天的星斗,拖着沾满泥浆的工靴,叽叽喳喳地回到板房。那叽喳声,是青春的元气,是对一日工作的消解,也是对明日希望的铺陈。 不觉间,竟已两年。 大坝,高了,壮了,有了顶天立地的模样。我们这群人,仿佛也同它一道,被时光浇筑着。小穆成了看一眼混凝土面色便知内里“寒热”的“老中医”;小杨画的图纸,再严苛的师父也挑不出几个刺儿;小王调度的“粮草”,总能恰恰好赶到最需要的时辰;而我笔下的文字,似乎也少了几分浮泛,多了几分沉实与温度。 只是,笑盈盈的脸背后,谁没有吞下过眼泪呢?想家时,便对着手机里定格的团圆饭发呆;委屈时,只能将一声叹息混着西北风咽下。无数个夜晚,当城市的同龄人在霓虹下畅想未来时,我们的未来,正与手边冰冷的钢板、密集的数据、待写的文稿,一同在灯下静静地生长。月光是常客,清冷冷地铺在图纸上,洒在键盘上,也漫进思乡的梦里。我们与月光相伴,并非为了吟风弄月,而是将青春这本该飞扬的银辉,一寸寸地,都夯进了这实心的、沉默的坝体里。 鲁迅先生曾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脚下,本也没有坝。是一代代人,将青春、汗水,乃至生命,当作一颗颗石子、一抔抔泥土,在这里堆积、夯实,才走出这条拦河蓄水、润泽千秋的路来。我们不是开创者,我们只是这漫长征途上,新来的一群赶路人。辞家千里,离乡又远一程,为的便是将这路,接续下去,走得稳些,再稳些。 此刻,夜色又如两年前那般笼罩下来。但工地上那一片灿烂的“热闹”依旧,甚至更为磅礴。我知道,那光里,有我们二十二粒“豆子”发出的、微茫却倔强的一点光。那沉浑的轰鸣声里,也混合了我们日渐坚定的心跳。 大坝正年轻。我们,也正年轻。这离家千里的山河,如今再看,已不只是他乡。 |
|
|
|
| 【打印】 【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