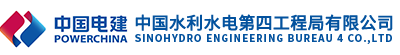折叠的时光 |
|
|
|
|
今年冬至的饺子,包得有些不同。食堂里早备好了两大盆馅儿,一盆是北方经典的韭菜猪肉,肥瘦相间的肉糜裹着斩得细碎的青叶子;另一盆是韭黄鸡蛋,金灿灿的颜色里透着家常的亲切。面是食堂大师傅提前和好的,一摞摞搁在案板上,用湿纱布盖着,怕被坝上这干烈的风吹皴了皮。空气里浮动着葱姜的辛香、麻油的醇厚,还有面粉那踏踏实实的、微微发甜的气息。这气息像一条温暖的河,一下子就把人裹了进去。 我的手指触到那微凉而柔软的饺子面时,心里那点“说不上来的感觉”,忽然就找到了一个着力点。三年了,同样的冬日,同样的活动,手指的记忆却比心思来得更直接。不用看,拇指与食指便自然地寻到那面皮的边缘,一捏两折三折四折,一个敦实实的麦穗饺便立在掌心了。这手艺,还是第一年冬至时,跟着生产部的小麻姐姐学的。她是青海姑娘,手巧得很,褶子匀称得像用尺子量过。她那时一边包,一边用青海话说着:“冬至不吃饺子,耳朵要冻掉哩!”哄堂的笑声,仿佛还能听见余音,可一抬头,原来她坐着的位置上,正坐着个眉眼尚带些学生气的年轻人,正笨拙地试图把裂开的饺子皮捏拢,鼻尖上还沾了点儿面粉。 这便是那“新面孔”了。他们眼里有着我们当年一样的、新鲜而略带茫然的光,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问着“这个阀门往左是开吗”“图纸上这个标高是不是有误”之类我们曾经也问过的问题。而我们这些“老人”,三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起初离校门的青涩,却已足够磨去一层。皮肤糙了,嗓门大了,走路的步子也踏得更实,更惯于在机器的轰鸣里扯着嗓子说话,在寒风里就着灰土咽下盒饭。我们成了他们口中的“师傅”,成了知道库区哪个角落背风、晓得拌合站老师傅最爱抽什么烟的人。这身份的转换,起初是不自知的,直到在这样的场合,看着他们,才恍然惊觉——原来那条名为“青春”的河,我们已经涉过了一段不短的水程。河岸的风景变了,我们的倒影,也不再是当初的模样。 我的目光不由得飘向窗外。透过蒙着水汽的玻璃,越过食堂前那片压着霜的空地,便能望见我们亲手“堆”起的“山河”。那座电站,就沉默而巍然地矗立在冬日的天幕下。三年前的冬至,我第一次参加这活动时,窗外还是一片莽苍。只有勘探时立下的红色小旗,在无遮无拦的野风里孤零零地飘着,远处是铁青色的山脊线,像大地沉默的骨骼。我们包着饺子,聊的是即将开挖的基坑有多深,截流的龙口该怎么安排。那时心里揣着的,是一张宏伟却冰冷的蓝图,是对未知工程的兴奋与忐忑。饺子吃在嘴里,味道是滚烫的,心思却飘在寒风呼啸的旷野上。 第二年,窗外已是大不同的景象。坝体的雏形已经起来,巨大的混凝土墙体像从大地深处生长出的灰色堡垒,起重机巨臂林立,车辆穿梭如蚁。包饺子时,手上沾着面粉,嘴里聊的已是浇筑的温控、灌浆的压力。那次的饺子馅好像咸了些,大伙儿一边喝水一边笑骂,可看着窗外那日益成型的庞然大物,心里头是满当当的、快要溢出来的成就感。那是一种创造者的、近乎父亲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的满足与焦灼。 而此刻,窗外的一切都沉静下来了。主体工程已然完工,电站像一头休憩的巨兽,安静地伏在山谷之间。它的线条是那样硬朗而流畅,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下,泛着混凝土特有的、坚实的光泽。没有穿梭的车辆,没有鼎沸的人声,只有它本身,带着一种完成使命后的、庄严的寂静。三年,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矗立,一千多个日夜里,我们的青春、汗水、争执、欢欣,仿佛都被搅拌进了那成千上万吨的混凝土里,浇铸成了这沉默山体的一部分。它不再只是图纸上的线条,报表上的数字,它是我们生命中被开凿出的一段峡谷,一条我们自己用岁月汇成的、更为沉静的河流。 锅里的水第三次沸腾了,白色的蒸汽汹涌地顶起锅盖,食堂里弥漫开煮熟面皮与馅料融合的、令人心安到几乎鼻酸的丰腴香气。第一盘饺子出锅了,白胖胖、热腾腾地堆在盘里,薄皮隐隐透出内里馅料的颜色。大伙儿一拥而上,笑声、筷子的碰撞声、被烫到的吸气声,瞬间闹成一片。我也夹起一个,蘸了点陈醋,送入口中。面皮的柔韧,馅料的鲜香,汁水的滚烫,一下子在舌尖炸开。这味道,与第一年、第二年,似乎并无不同,可咽下去,那暖意一路氤氲到胃里,再慢慢扩散到四肢百骸时,却品出些更深的东西来。 那不只是食物带来的温暖,是在这远离故土的僻远之地,一群原本陌生的人,因一项共同的事业而聚拢,在古老的节令里,用最朴素的方式,彼此确认着温度,确认着“在一起”的踏实。这饺子里,包进去的是韭菜猪肉,是韭黄鸡蛋,又何尝不是这三年的寒来暑往,风霜雨雪,是那些想家的夜,攻坚的关,还有此刻身边这些熟悉或正在变得熟悉的面孔?我们吃下的,是一段共同浇筑的时光。 窗外的电站依旧沉默。但我知道,当来年春汛涌动,山间的积雪融化,万千细流汇入这我们亲手打造的容器时,它将不再沉默。它将开始低吟,开始轰鸣,将沉睡了千万年的水的力量,转化为照亮远方城市的光与热。我们的河流,将以另一种形态,开始它永恒的奔流。 而我们的河流呢?电站建成了,一些人会留下,更多的人,或许像很多已经离开的人一样,奔赴下一个“尚义”,在另一片荒芜上,再次开始从无到有的创造。这或许就是工程人的命运,也是工程人青春的特质——我们永远在建造“完成”,自己却永远在“路上”。但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曾在此处,将青春拧成钢筋,将岁月夯为坝体,我们创造了一条能发电的、物质的河;而我们每个人,也从此成了一条河,身上带着“尚义”这一段峡谷的深刻地形,带着混凝土的坚定与饺子的温热,继续向着生活的、事业的下游,不舍昼夜地流去。 盘子里的饺子渐渐见了底,身上的寒意早已驱散。我喝下最后一口饺子汤,那原汤化原食的暖意,通达而舒畅。天,已经黑了。但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照在电站崭新的闸门上,也照在我们即将踏上的、各自的新征程上。 那条河,在饺子的褶皱里,在我们生命的河床里,正浩浩汤汤,流向灯火斑斓的远方。 |
|
|
|
| 【打印】 【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