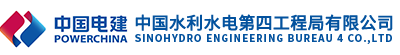四局人在此,与风对话 |
|
|
|
|
从西宁曹家堡机场起飞的那一刻,我并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一段怎样的行程。飞机在青藏高原的晨光中缓缓升空,舷窗外的城市渐渐缩小成一幅斑驳的地图。一个半小时的飞行,却仿佛跨越了两个世界——从湟水谷地的温润到柴达木盆地的苍凉,云层下的大地如同被时间遗忘的古老卷轴,一寸寸展开它最原始的容颜。 花土沟机场小得令人心悸,跑道尽头就是天地相接处。当双脚踏上这片海拔三千米的土地时,干燥的空气瞬间抽走了肺部所有的水分。来接站的车辆上覆盖着一层细密的沙尘,像是从远古走来的化石。 司机是个沉默的甘肃汉子,装上从西宁托运来的慰问品,他递给我一瓶矿泉水,说着“还有三百公里,四个多小时车程,全是老石油路,今晚只能先住到冷湖镇明天一早再出发”。 车辆驶出机场围栏的瞬间,现代文明的最后痕迹消失了。车窗外展开的是一片真正的无人区,不是地理课本上那种诗意的荒原,而是被烈日和风沙反复鞣制的、结痂的大地。盐碱地泛着病态的苍白,像被抽干血液的兽皮,偶尔出现的骆驼刺不是绿色,而是铁锈般的暗红——那是植物在极端环境下分泌出的防御性色素。 磕头机出现在地平线时,我正在喝第二瓶矿泉水。它们不像想象中那样密集,而是像被随意撒落的黑色火柴盒,每台相隔至少五百米。这些由钢铁与橡胶构成的机械生物,以每分钟四次的频率永恒地点头,仿佛在向大地深处某种看不见的存在致意。 冷湖镇出现在黄昏最稠密的光线下。这个因石油而兴的城镇,像被随手抛洒在戈壁上的积木,从远处看只有三种颜色:白色(集装箱改造的宿舍)、蓝色(报废的储油罐)和红色(永远崭新的中石油标志)。 真正震撼是在冷湖老基地遗址。当车辆转过最后那个弯,突然出现的不是城镇,而是一片钢铁的废墟。数千栋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苏式砖房像被时间啃噬的骨骼,整齐排列在逐渐暗下来的天幕下。最完整的那栋门楣上还留着“中国石油工业部”的浮雕,如今被风沙磨得只剩轮廓。 夜里住在镇上新开的宾馆,前台小伙是甘肃张掖人,他给我房卡时说:“这几天算暖和的,才零下十八度。” 我突然意识到,从中午花土沟机场的路灯,到此刻冷湖镇的路灯,这一路上所有的光都是人造的——我们用了六七个小时,飞机加汽车,竟没能走出人类在青海境内用工业之火照亮的范围。 第二天离开时,发现宾馆门口贴着张褪色的宣传画:一个穿工服的青年站在磕头机旁,背景是升起的太阳,下面印着1980年代的标语——“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石油事业”。那个青年的笑容已经被紫外线漂成惨白,但他的眼睛依然望着远方,望着这片至今仍在持续献出黑色血液的古老土地。我想,或许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奉献,才让我们的飞机汽车无论如何奔驰,都永远走不出这片被热血与原油共同浸透的辽阔。 早上我们出发时,司机指了指仪表盘上显示的室外温度:零下25摄氏度。司机师傅的声音混着发动机轰鸣,“前面没路,只有车辙”。 车辆驶入G315国道支线时,最后一棵骆驼刺从后视镜里消失了。天地忽然变得如此简单——上方是铁青色的苍穹,下方是灰黄色的戈壁,中间横亘着一条被风沙啃噬得支离破碎的土路。车轮碾过盐碱地时扬起白色粉末,像给荒芜的大地撒上一层防腐剂。偶尔有风卷着沙粒抽打车窗,发出细密的噼啪声,那是荒原最温柔的警告。 黑独山出现在了清晨光影里。这座由黑色砂岩构成的孤峰,像被天神随手掷下的煤块,在亿万年的风沙雕琢下呈现出尖锐的棱角。司机说蒙语称它为“哈拉乌苏”,意思是黑水之地。山体表面布满蜂窝状的蚀痕,每个洞穴都藏着古老的秘密。当夕阳将山体染成暗红色时,那些洞穴突然变成了无数只凝视的眼睛——这是荒原最庄严的仪式,让每个过客都感受到亿万年地质变迁的重量。 穿过黑独山后,手机信号也时有时无。远处出现一片转动的风机,在荒凉的戈壁,排着整齐的队伍迎接我们。随着一排集装箱营地的出现,司机踩下刹车,“到了”他说。 海西风电项目部的集装箱营地像艘搁浅的方舟。二十几间白色厢房围成矩形,不远处柴油发电机房,它持续不断的轰鸣声成了荒原上新生的脉搏。早上的十点,项目部的接待室地面还有结冰。项目副经理樊甲勇说,“有时候风也很大,夜里躺在集装箱床上,听见风从钢板缝隙间挤入的声音。” 不远处,那些高达百米的钢铁巨人,此刻正安静守护着它们脚下这个临时的人类聚居地。而此刻在周围荒原上,只有风电机组转动的叶片划破空气的声响——那是人类向自然递交的某种契约,用钢铁的骨骼去捕捉风的灵魂。 风机吊装现场是荒原上最壮丽的舞台。主吊是1300百吨级的履带吊,伸展的臂架像只钢铁螳螂悬停在空中。当33.5吨的叶片被缓缓吊起时,整个荒原都安静下来——连风也屏住呼吸。现场指挥员站在百米开外用对讲机喊话,声音混着电流声变得像某种古老咒语:“左偏五度...保持...下降...”当叶片与轮毂对接成功的瞬间,所有工人突然同时摘下安全帽向天空挥舞,像一群向太阳致敬的原始信徒。 刚到那天清晨,最后一台风机刚好吊装完成。项目经理老杨他们提前完成所有40台风机的吊装,这意味着这个团队从荒漠的三四十度的高温酷暑一直干到了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在荒原上坚守和奋斗了127个日夜。 当返程再次经过黑独山时,我忽然注意到山体背风面积着细沙,它们形成了完美的流线型波纹,像被冻结的波浪。这些波纹会存在到下一个地质纪年,而此刻在它们上方,新装的风机正缓缓转动首批叶片——荒原终于学会了用人类的方式呼吸。 飞机腾空而起时,我看见那些白色巨人渐渐缩成银色图钉,最终融化在盐壳与天空的交界处。机长广播说西宁温度零上四度,而我知道,在柴达木西北的某个角落,有群穿红色工装的四局人正以自强不息、勇于超越奋斗的姿态,继续顽强拼搏、勇毅前行去完成下一阶段的并网发电任务。他们的影子投在比时间更古老的荒原上,像一串被风精心雕刻的象形文字——上面写着:四局人在此,与风对话。 |
|
|
|
| 【打印】 【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