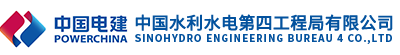除雪箱梁上,留白一隅间 |
|
|
|
|
雪是忽然来的,在黄昏与夜晚模糊的边界上。起初只是疏落的几片,试探似的,落在测温仪的屏幕上,化成一星转瞬即逝的湿痕。后来,风起了势,裹挟着亿万片羽毛,从混沌的天穹倾泻而下。不过是一夜之间,平漯周高铁项目部,连同它周遭无垠的原野、静默的桥墩、成排的箱梁,都服服帖帖地盖上了一床厚实而蓬松的棉被。世界被一场大雪,简化为黑白二色,只剩下轮廓与弧线,声音也被吸走了,天地间唯有簌簌的落雪声,绵密而永恒。 这寂静的统治,在第二天黄昏下班时分,被我们亲手打破。不知是谁先捏了第一把雪,那凉沁沁的触感,像一道闪电,击穿了连日枯燥报表与冰冷数据筑成的堤坝。沉寂的篮球场骤然苏醒。雪团在空中划出凌乱而欢快的弧线,炸开在工装后背,绽成一朵瞬凋的白花。笑声、惊叫、佯怒的呵斥,混着奔跑时踩雪的“咯吱”声,将这方被工程术语填满的天地,搅动得热气腾腾。有人滚起了巨大的雪球,那是雪人笨拙而洁白的身躯;有人寻来枯枝作臂,两颗乌黑的石子嵌下去,便有了孩童般憨直的眼神。最畅快的,是寻着一处缓坡,将一块废模板当作雪橇,几人轮流坐着,呼啸而下。风夹着雪沫刮过脸颊,那一刻,耳畔没有泵车的轰鸣,只有自己心跳与速度的合奏,仿佛顺着这洁白的滑道,一下子溜回了遥远的、没有桩号与标高的童年。 欢腾的痕迹,在箱梁的雪被上显得尤为珍贵。但浪漫需为责任让路。第三日清晨,阳光惨白地照在盈尺的积雪上,运梁车的履带需要一条干燥安稳的通道。指令简洁,响应却如臂使指。物资库房前排起了队,铁锹与扫帚的木质长柄摩挲作响,像出征前清点兵刃。我们登上那巨大的箱梁,它此刻成了一条横卧于天地间的、纯白的跑道。四人一组,自成段落。铁锹在前,铿锵地啃开坚实的雪壳,铲出通道的筋骨;竹扫在后,唰唰地拂去残留的碎玉,露出混凝土灰蓝的本色。呵出的白气在空中交织,额角蒸腾的热气融化了睫毛上的霜。没有指挥,却默契得像一套运转已久的机械:你铲到我跟前,我自然接上扫的工序;他堆起的雪堆,立刻有人接力清走。只有铁器刮擦混凝土的锐响,扫帚划动的沙沙声,以及间歇的、简短的提醒:“这儿干净了!”“往左!”枯燥的劳动,因这共同的、单纯的目标,竟生出一种流畅的韵律感。不过一个上午,这条钢铁长龙背上的积雪便被拦腰截断,露出一条笔直而干燥的深灰色轨迹,像大地为自己划下的一道清晰坚定的标线。 下午,我们转向项目部门前。篮球场的雪,因昨日的嬉戏,变得瓷实而斑驳。清理起来,更像是一场精细的修复。铁锹下去,需多用几分巧劲,以免伤及硬化地面。扫帚掠过,也要格外轻柔。然后,我们看见了它——昨日那个被我们赋予生命的雪人。它依旧站在那里,树枝手臂微微张开,石子眼睛天真地望着我们。挥舞的扫帚和铁锹,在它面前齐刷刷地改变了轨迹。人们不约而同地绕开了它,仿佛它并非一堆无心的雪,而是一个被默许的、有尊严的住户。扫清的场地不断扩大,边缘规整如画,唯有那个角落,保留着一小片纯净的隆起,和那个沉默的、胖乎乎的守望者。 清扫完毕,大家散了。我独自站了一会儿。夕阳从云层裂隙漏下,给冷却的工地镀上一层柔和的金晖。庄严齐整的项目部板房,灰白肃穆的庞大箱梁,构成了一幅理性而坚硬的图景。而在这一角,那憨态可掬的雪人,静静地立在光洁的场地边缘,像乐章末尾一个顽皮的、不协和却又可爱的音符。它让这一切宏大叙事,忽然有了一抹人性的温度,一点天真的破绽。这破绽并非瑕疵,反是这严整世界里,一扇得以呼吸的窗。 雪终于停了。天空澄澈,像一块无限伸展的淡青色玻璃。明日,一切将重归严谨的轨道:运梁车的履带会压过我们清扫出的路径,泵车的轰鸣将再度唤醒凝固的时间,所有的计算与标高,将继续它分毫不差地延伸。但总有一些东西,被一场雪悄悄地改变了。那个立在操场一角的雪人,它圆滚滚的躯体与略显滑稽的五官,并非对庄严的冒犯,而是一种温存的“修正”。它让一个由钢铁、混凝土与数据构成的世界,获得了一次柔软的呼吸;让一群缔造通途的人,在严谨的图纸之外,共同守护了一个毫无用处却无比天真的坐标。 那便是雪留给平漯周最轻也最重的礼物——在通往未来的坚硬路基旁,始终为一点柔软的初心,留着一小块洁白的位置。 |
|
|
|
| 【打印】 【关闭】 |